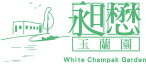從宜蘭看天下

越南移民(下)
◎羅漪文
我出生的時候,漫長而激烈的戰爭才剛結束不久,鵝黃色的西貢市頓時黯淡無光,夜晚的街道巷弄皆因宵禁和電力不足而陷入漆黑,不只是我們一家,周遭所有人都過著慘淡拮据的生活。
然而,也因為天黑,抬頭即可望見星星布滿天空,碩大晶亮彷彿伸手可觸。
星星使我對黑夜不甚畏懼,而我媽媽則相反,她忐忑不安的摟著我入睡,深怕公安隨時敲門,「他們想要進來就進來,掀開蚊帳,看看裡面睡覺的人。」
就在某一次,公安無預警登門,他們大肆翻找家中物件,最後在衣櫃裡找到兩百元美金,於是沒有任何解釋就將爸爸帶走,後續連審判形式都沒有。
爸爸從此待在勞改營七年,留下媽媽和襁褓中的我相依為命。
一九八六年,為了證明其改革開放的誠意,越南政府釋放所有「偽政權」、「舊制度」的勞改犯人,爸爸才重獲自由。
五年後,爸媽兩人變賣僅有的小房子,湊錢買了機票,帶著我和妹妹告別越南。那是一九九一年,靈活的台商在越南開放之初就前往投資,爸爸因為會說中文而找到在台商公司的工作,但他們仍想離開。
爸爸後來承認,他想要離開那片傷心之地,也希望孩子能有機會接受中文教育。
窩居在木柵的我們,從未想過有朝一日會遇到越南女孩。他們大多數非常年輕, 十八、九歲青春冒險,遠渡重洋與台灣人結婚,適應婚姻的同時,適應異國文化,其中艱辛難以言明。
爸媽販售雜貨時常懷著某種憐惜,詢問她們的娘家在哪裡,在哪一條河流邊上,有沒有比我爸爸的故鄉堅江省迪石市更加遙遠?
在後來,加速推進的全球化浪潮又將北越的勞工送來台北。雜貨店出現新的顧客令爸媽和其他華裔移民相當意外,後者大概是沒有心理準備某一天竟會遇到「勝利的一方」。
當年,北越人挾著政權的優勢來到南方,變更了城市的名字,以強勢的意識形態掃蕩各個街區。在我們居住的巷子裡,來了一對北越夫妻接收了華人留下的屋子。
夫妻倆是黨員幹部,白天騎著腳踏車去上班,晚上回家鎖門,鮮少與鄰居互動,而作為「被解放者」的鄰居們與之保持客氣的距離。
所以,當北越勞工出現了,隱隱掀起某種不解與心知肚明的嘲諷:「為何南越姑娘必須結婚才有機會出國,而北越人可以出口勞動?大概又是革命後裔的福利吧!」
來台灣工作的北越人,有些住在偏僻的農村,方音甚濃。而早期華裔移民和「台灣的媳婦」(Dâu Đài)所說的越南語,腔調和北越人說的不僅不一樣,甚至年長的華裔還保留著「解放前」時期的詞彙。
南北雙方偶爾出現溝通不順暢的情況,但有什麼辦法?能夠協助翻譯的,也就是華裔和南越姑娘了。
我生長於南越,對南方文化充滿感情,加上有一段時間裡電視台密集播報「越南新娘」被虐待的新聞,使我掛念著年輕的南越姑娘們需要協助。然而,歲月悠悠,當我在二○一六年學習司法通譯課程時,班上大多數的南方姑娘已經熬過了他鄉異地的生活考驗,活潑地出來學習進修、考取各種執照來肯定自我。
因此,擔任司法通譯多的是「台灣的媳婦」,所服務對象反而是大部分為北越勞工。
於是,可以理解偵訊室裡的男人詢問我「是不是嫁過來的?」不只有他,很多勞工常常會這麼問。
延伸閱讀...越南移民(上)
(摘自:寶瓶文化《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》)
(圖/三星花月夜,畫家張堂龲提供,IG:@tarngkuh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