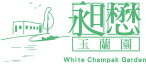從宜蘭看天下

越南移民(上)

◎羅漪文
移民署專勤人員盯著電腦螢幕,將筆錄內容對過一遍,按下列印紐,起身到外面大辦公室拿取印出來的紙本,偵訊室只剩下我和一名北越中年男人。
他的左手被固定在辦公椅的扶手上,連人帶椅子側過身來,以試探的眼神看著我,問:「你是結婚過來的嗎?」
我搖頭:「不是。」
見到他的表情有些困惑,我補充:「我從小就來了。」
他又問:「那你是城市裡的華人?」
我點點頭。
多年以前,我們全家還住在越南西貢。在越南語裡,「城市」一詞專指西貢。一九七五年,越戰結束,美軍匆匆撤離以後,西貢改成胡志明市。
經歷了閉關鎖國逾十年,越南政府終於宣布實施改革開放。爸爸的兒時鄰居從澳洲首次返回故里,探望親友,短暫相見,旋即告別,爸爸帶著我們至市郊新山一機場送行。
鄰居叔叔一家三代在南方「被統一」不久,及當機立斷偷渡離開,定居雪梨,那時的船費以黃金計算,按媽媽的說法:「價格一直漲,最高每個人要六兩黃金。我們家居住的巷弄小屋只值二兩。」
我十三歲抵達台北。在那之前,經過越南公立學校,接受一到六年級的教育。當時西貢的華校全數遭勒令關閉,許多華人家庭寧可讓孩子待在家裡,我爸卻不以為然,除了語文,越南學校還有數學、生物、物理、地理等其他知識呢!因為有上學的緣故,我順利通過台灣教育部的檢定考,編入國中二年級。
跟其他移民小朋友相比,我相對容易適應台灣的課程內容,同時又保留著越南書面語的記憶。
媽媽在台北越南移民聚集的木柵區開東南亞雜貨店,我和妹妹輪流在店裡幫忙。
越南、印尼、泰國、菲律賓、柬埔寨等各國籍配偶及勞工在店裡來來去去,除了購物,偶爾會有人拜託抄寫中文地址、叫計程車,或寫下「我想買咳嗽藥」、「避孕藥、二十八顆一片」之類中文紙條。
最挑戰的一次,是從越南嫁過來的T姊持著從土地公廟裡求來的籤詩,要求翻譯。
我問:「妳用什麼話跟土地公求?」
T姊理直氣壯:「越南話啊,反正神靈都會聽懂吧?」
「有道理!」
但籤詩有古代典故啊,我費勁翻譯了一陣子,再確認:「所以,妳覺得土地公給的籤很準嗎?」
T姊連連點頭:「有耶,很準耶!」
我以為,這些只是隨手協助而已,從沒想過後來竟也有機會去機關單位,替越南移民工進行翻譯。
大約在一九九○年代中期以前,移居台灣的越南、寮國、柬埔寨三國的移民,大多是華裔。人們搭飛機飛往泰國曼谷,再轉乘由中華民國政府派來的華航來到台北。我們一家四口循著同樣的路徑,定居木柵。
木柵有一大片名為「安康社區」的平價國宅,幾十棟灰色四層樓的老公寓。中南半島的移民帶著逃避戰亂與貧困的恍惚心情住進來,努力尋找工作,安頓家人,彼此之間以廣府話夾雜越南語交談。
我的爸媽初來乍到,除了無法從事工地體力活之外,做了各種移民會做的工作,例如縫製成衣、電子零件工廠作業、大廈警衛等等,最後決定在安康市場租下攤位,販售東南亞調味品食材。
幾年之後,開始出現嫁給台灣人的越南南方女孩。她們幾乎都來自九龍江平原,華裔移民和女孩們以南方腔溝通,無絲毫障礙。女孩們對華人並不陌生,畢竟自清朝初期以來,拒絕降清的「明鄉人」最早投奔而來,獲得越南阮氏朝廷許可定居墾荒。
華人於是漸漸在南越開枝散葉,九龍江平原的越南語甚至摻雜了許多潮州話和廣府話的詞彙。
南方女孩因能在台灣聽見越南話而安心下來,至於華裔則從女孩們那裡,憶起遼闊無邊的稻田、椰子樹以及街區午後的滂沱大雨。
未完待續...越南移民(下)
(摘自:寶瓶文化《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