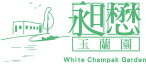從宜蘭看天下

【讀者,你到底想怎樣?】
從我小時候接觸「新詩」以來,就一直有種深深的困惑:為什麼那些看起來只是隨意排列的清淡文字,可以自稱「詩」?它們不像古典詩,一讀起來就能感受到「這不是日常語言、確實特別美」,有些新詩的文字甚至淡如清水,比如 吳盛 的名作<甜蜜的負荷>:
┏
阿爸每日每日的上下班,
有如自你們手中使勁拋出的陀螺,
繞著你們轉呀轉;
將阿爸激越的豪情,
逐一轉為綿長而細密的柔情。
┛
當然,課本和老師會告訴我:新詩就是為了改革古典詩艱澀難懂、格式僵化的問題,才往這種自然、平淡的方向發展。聽起來很有道哩,我被說服了。這大概既像是大魚大肉吃慣了,偶爾也會想吃清粥小菜吧?但「好景不常」,我接下來又讀到了 洛夫<石室之死亡>:
┏
祇偶然昂首向鄰居的甬道,我便怔住
在清晨,那人以裸體去背叛死
任一條黑色支流咆哮橫過他的脈管
我便怔住,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
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
┛
吳盛的文風輕淡,幾乎看不出有什麼文字技巧;洛夫這首相反,初讀此詩之時,除了「好像很有技巧」,我完全看不懂。等等,不是說好了新詩不要艱澀,崇尚自然平淡嗎?洛夫這樣的詩,比「床前明月光,疑似地上霜」之類的古典詩還要艱澀得多,這顯然跟前面的說法矛盾。更矛盾的是,這兩首詩還都是名詩人的名作,也就是說,新詩的專家們認為兩種詩風都很好──所以新詩到底想怎樣?是寫得簡單易懂,還是寫得詰屈聱牙?
我們接著再來看下列兩首詩,
(1)
那河畔的金柳,是夕陽中的新娘;
波光里的艷影,在我的心頭蕩漾。
軟泥上的青荇,油油的在水底招搖;
在康河的柔波裡,我甘心做一條水草!
(2)
潮來潮去
左邊的鞋印才下午
右邊的鞋印已黃昏了
第一首,是民國初年 徐志摩的<再別康橋>。第二首,則是 洛夫 的<煙之外>。兩者發表的時間相差三十多年,中間就隔著一份「現代派六大信條」。我們可以看到,兩首詩的感覺完全不同。沒有經歷過「信條」洗禮的徐志摩,會在寫出意象(金柳、青荇、康河)的同時,也把自己的感覺寫出來,直接表明「我甘心做一條水草」。但是經歷過「信條」洗禮,深受現代派影響地洛夫,他雖然同樣寫出了意象(潮水、鞋印、黃昏),但我們看不到任何直接寫出感覺的句子。
「困難」或「平易」的殘酷二選一,一直是人們討論新詩時最關心的問題,在文學史上的各個論戰也不例外。一般文學讀者更是有一種矛盾心態:如果新詩寫得太平易,就會被譏笑為「分行的散文」、沒有詩意;如果新詩寫得太困難,就會被指責是詩人在假鬼假怪,無法引起共鳴。老實說,如果我是詩人,可能也想反問讀者「到底想怎樣」。然而,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種「新詩現象」,其實也是在文學論戰中形成的,特別是發生於一九五〇年代的一系列「現代派論戰」。
欲知後事如何,請參閱《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:台灣文學百年論戰》p.188頁。
(摘自《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:台灣文學百年論戰》,作者/朱宥勳,出版/大塊文化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