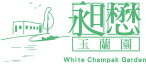從宜蘭看天下

🍂 落葉歸根 vs 落地生根 🌱
朱天文在《想我眷村的兄弟們》提及,每次一到清明節,她都會偷偷躲在遠處看著「臺灣人」祭祖掃墓,當時年紀小,她和姐妹們都覺得很新鲜,有時甚至會把墓園當成玩耍的地方,邊玩邊偷窺人家掃墓,那些本省人奇怪的供品或祭拜的儀式、或悲傷肅穆的神情,令他們暗自納悶,但是,當她回家看到父母親在後院默默燒著紙錢,因為不確知家鄉親人的生死下落,只得語焉不詳的寫著是燒給〇氏祖宗的,那表情也極度錯綜複雜,不敢悲傷飲泣,臉上卻布滿日趨遠去但記憶猶新的憶往。
朱天心回憶當時的情景說,「那時候兩岸尚未開放探親,父母親無法和自己的爸媽連絡,骨肉分離,生死未卜,那種至親之痛是言語難於描繪的。」後來她終於明白在那些年間,父輩們為何從未把島嶼當作落腳生根處,「原因無他,清明節的時候,他們並無墳可上。」「原來,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,是無法叫做家鄉的。」
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
故鄉是俺心中的墳,裡面住著父親母親,
天天過著寒食清明,冷雨紛紛
── 管管
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
陳芳明教授認為,若沒有眷村的話,本省跟外省人應該早就融合了,可是沒辦法,因為他們還是需要一個地方住,眷村也是集體管理的。國民黨為了方便管理,不要這些族群在一起,眷村有自己的認同,就比較能夠管理。八二三炮戰跟越戰使得臺灣人慢慢成為命運共同體,戰爭的威脅,還有反共的經驗,使我們慢慢去理解這些東西。
陳芳明教授以其寬闊的心胸與嶄新的視野,再加上「後殖民」、「族群」,「性別」的三大議題,避開各種沙文主義,重新建構了《臺灣新文學史》(臺北:聯經,二〇一一)。在這悲憫的自我期許下,陳教授在歷史分段中,不很刻意的將許多外省籍的作家、眷村作家列於二戰後的文學分期裡,使得「眷村文學」也獲得臺灣鄉土文壇的認可。眷村人士的文學心血,不再被拋之於本土之外。
繼之,臺灣文學館在民國一〇二年出版了一套《臺灣文學史長篇》,其中第二十九集,為楊佳嫻著《方舟上的日子──眷村文學》,到此,正式將眷村文學併入「臺灣文學」之列。
❐摘自眷村雜誌《槍桿與筆桿下的眷村文學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