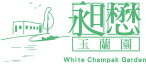從宜蘭看天下

馬奎斯談寫作和盛名之累
孟多薩:你在《枯枝敗葉》和《百年孤寂》之間的幾部小說(即《沒人寫信給上校》、《惡時辰》、《大媽媽的葬禮》),手法突然變得比較寫實,有點綁手綁腳的,在語言跟結構上似乎都受到限制,絲毫不見魔幻與無法無天的奔放。你如何釋這樣轉變?
馬奎斯:寫《枯枝敗葉》的那個時期,我的信念是每一部好的小說都應該是將現實置換為詩學上的圖景。不過如果你記憶猶新,那本書發行的時候,哥倫比亞正值生靈塗炭的血腥政治壓迫。有些好戰的朋友對我說的話,帶給我很深的罪惡感,他們說「你的小說裡什麼都沒有譴責,也什麼都沒有揭露」。儘管現在看來這樣的見解太過簡化,而且有所誤解,但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應該更關注國家當前的政治與社會現實,所以我暫時遠離了我最初的文學理念。所幸我現在又再次回到原先的方向,不過當時我可是冒著一敗塗地的風險。
孟多薩:是什麼促使你改變方向?
馬奎斯:我仔細思考了我在做的事,想了很久終於得到結論。我的使命所繋並不只單單在於我國的政治和社會現實狀祝,而應該是整個世界的現實狀況,並且不應只是特別偏好或貶抑哪一個方面。
史崔佛:諾貝爾獎得主難道不能豁免於日常生活的瑣務嗎?
馬奎斯:獲得諾貝爾獎唯一的好處是不用排隊。只要有人發現你在排隊,他們就會直接把你帶到最前面。
史崔佛:這真的是唯一的好處嗎?
馬奎斯:享有聲名就像駕駛巨無霸客機,這種事需要格外小心細膩處理,當然我沒什麼好多抱怨的。諾貝爾獎頭銜意味著某種尊榮,所以對於那些你覺得很煩的人,現在你已經不能愛怎麼說就怎麼說了。
當我發現有位朋友把我的私人信函賣給某間美國圖書館的時候,我知道自己的生活在《百年孤寂》出版之後已經變得不一樣了。我不再寫信,因爲這樣就不會再有人賣信。聲名對我的個人生活來說完全是一場災難,彷彿你可以藉由圍繞在身邊的人數,度量孤寂的指數。圍繞在你身邊的人愈多,你就感到自己愈來愈渺小。
史崔佛:一九六七年《百年孤寂》出版之後立刻轟動當世,享譽二十餘年至今。您應該已經很習慣了。
馬奎斯:我確實在先前已有聲名,但沒什麼人注意到我,不過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一切就不再是那麼回事。我有項一直都很想實行的計畫:開車到某個哥倫比亞的小鎮,走出車外認識這個小鎮,然後好好寫一篇報導介紹這個小鎮。不過我領悟到一件事:到了第三天,全哥倫比亞的通訊特派員都會擠到這個小鎮看我寫這篇報導。我就是他們的新聞。
聲名幾乎毀滅我的生活,因爲聲名攪亂我對於現實的感受,差不多就像權力帶來的後果:迫使你自陷於孤獨,造成人際交流上的困難,最後與世隔絕。
(摘自《馬奎斯:最後的訪談》)
(圖片來源/天下雜誌:flickr.com/photos/albertoyoan)